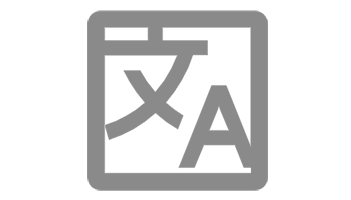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
出处
原文
郑子玄者,丘长孺父子之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嗛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嗛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则郑子玄之不肯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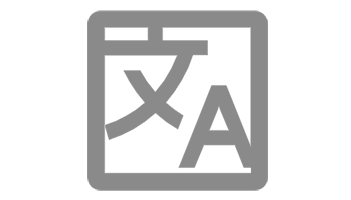
译文及注释
译文
郑子玄,是丘长孺父子常在一起作诗论文的朋友。他的文章虽然不及丘长孺父子,但品德朴实而且有知羞耻的心,不愿去讲学,也是位可喜人物,所以喜欢他。他完全没有亲身见过颜回、曾参、子思、孟轲,也没有亲身见过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只看到今天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人,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也确实像他们那样罢了,所以感到羞耻而不愿去讲学。不讲虽然是过错,但是使学者感到羞耻而不愿意去讲,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如像这样而作罢,那么今天讲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的道学家就该讨伐了。他以为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朱熹这些人都是口里讲着道德而心里想着高官,志在成为巨富;既然已经得到高官,成为巨富,仍然照样讲着道德,说着仁义;又跟着对人乱嚷乱叫说:“我想要劝勉讽戒社会习俗。”他认为败坏社会风气的,没有能超过讲周敦颐、程颖、程颐、张载、朱熹的人了,所以更加不相信。不相信就不愿意讲。既然如此,不讲也就不是过错了。
黄生经过这里,刚从京城去长芦去打秋风又眼着别处去担任新的职务。遇到了更有权势的官僚,便舍弃了长芦的长官,随即调转马头往北,而撞风冒寒,不顾年老,已经到了麻城,对我说:“我想游览嵩少,那个有地位的人也想游览嵩少,于是拉着我一起走,因此来到这里,但他已经在城里等着我,在这种情形下,我不能这里住上一夜了。回来的时候再经过这里,经过这里就多相聚几天再分别,现在太过仓促了,实在舍不得分别。”他的话是这样说的,但他的真心又是怎样的呢?我猜测他的内心实在是对在林那里捞油水难以割舍把。林三次上任做官的,黄生没有一次不跟着前往,去了回来一定满载,现在仍没有满足,好像饿狗想着隔日的屎一样,竟敢欺骗我说是想游览嵩少。他用游览嵩少山的名义隐藏到林云程处去打秋风来欺骗我;又担心林云程怀疑他打完秋风半路离开寻找我,于是用再用舍不得我李贽的原因,再来寻访李贽为理由来使林云程满意:真是名利双收,肉体享受得到满足,名声品行得到保全。我和林云程差一点都落入他的圈套而不能够察党,能不说他的手段太狡诈了吗!今天宣传道学的人,和他有什么不同呢!
可以看些所谓圣人其实和那些自称山人的那些人是一样的,只是有幸运有不幸运的不同罢了。幸运能写诗就自称为山人,不幸运不能写诗就不称自己为山人,称自己为圣人。幸运能讲良知,那么就自称为圣人,不幸运不能讲良知,那么就不称圣人而称自己为山人。这样翻来覆去,为骗世人和名利,名义上是山人心里却和商人一样追求名利,口里讲着道德而心里想着穿墙偷盗。已经是可鄙视了,为了掩盖打秋风的目的竟然标榜是游嵩少。以为别人是可以欺骗的,那就更加可鄙了。现在讲道德性命之学的道学家,都是和标榜游览嵩室山的黄生一样患得患失,而志气在于高官厚禄,美好的田宅,吉利坟地,庇护后人,都是在林云程那里假托理由舍不得李贽。子玄不愿意讲学,确实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了。
再说商人又有什么可以鄙视呢?带着数万资金,经历风浪波涛的危险,受到关卡上官吏的侮辱,在集市交易中忍受诟骂,辛苦劳累无法形容,所携带的很重,但是得到的却微不足道。然而还要和卿大夫们结交,这以后才才能获得利益而避开危害,怎么能够傲慢地坐在公卿大夫之上呢!今天这些所谓山人,名义上如同商人,但实际上没有一点资本被称为山人,却不是公卿的门不踏,所以是可鄙的。尽管如此,我难道就没有这种表现吗?怎么知道我没有商人的行为和想法,穿着佛教的外衣用来欺瞒世人,骗取名声呢?如有的话请对我进行责备、惩罚,我不袒护短处。即使如此,像他们那样患得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肯定是不会做的。
注释
郑子玄:与下句的丘长孺都是李贽在麻城时的朋友。
颜:颜回,又名颜渊,字子渊,孔子得意弟子。早亡。后世尊为复圣。
曾:曾参,字子舆。孔子弟子。以孝著称。传孔子之学,以授子思。后世尊为宗圣。
思:子思。孔子之孙,名伋。受学于曾子,后世称为述圣。
孟:孟轲,字子舆,子思的再传弟子,后世尊为亚圣。
周:周敦颐,字茂叔,号濂溪,道州营道(今湖南道县)人。北宋理学的创始人。
程:指程颢、程颐兄弟。世称“二程”,洛阳人。并为理学奠基人。
张:张载,字子原,凤翔郿县(今陕西眉县)人,人称横渠先生,北宋理学家,其学派称“关学”。
朱:朱熹,字元晦,号晦庵,婺源(今属山西)人。他把二程学说发展为完整的理学体系,为理学的集大成者,人称“程朱学派”。
哓哓(xiāo)然:争辩不休的样子。
厉:同“励”。
风:教化,感化。
黄生:其名及生平未详。
京师:这里指明代京都北京。
长芦:在今河北沧州市西。
抽丰:指找关系走门路向人求取财物。也作“秋风”或“打秋风”。
九江:今江西九江市。
麻城:今湖北麻城,时李贽在此讲学。
嵩少:河南嵩山的别称。嵩山西为少室,故称“嵩少”。
卒卒:同“猝猝”,仓猝。
林汝宁:指汝宁林知府。汝宁府,治所在今河南汝南县。
嗛:字或当作“赚”,欺骗。
山人:指隐士。
良知:孟子用以指天赋的道德观念。《孟子·尽心上》:“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后来王守仁据以提出“致良知”说,作为道德的修养方法。
穿窬(yú):《论语·阳货》:“其犹穿窬之盗也与!”穿,穿壁;窬,同“逾”,越墙。
赀:同“资”,财物。
释迦:释迦牟尼,佛教的始祖。这里指佛教。
参考资料:
1、章培恒,安平秋,马樟根主编;陈蔚松,顾志华译注,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 李贽文选译,凤凰出版社,2011.05,第50-55页
赏析
本文是李贽写给友人焦竑的一封书信。在这封信中,李贽对由宋代程朱理学发展而来的明代假道学,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文章先以郑子玄的“以讲道学为耻”与黄生式“名利两得”的假道学展开对比;又以“心同商贾”的山人与“口谈道德”的圣人其实一样,来衬托郑子玄的“可喜”与可贵;再进一步指出“欺世盗名”的假道学连商贾都不如的虚伪本质。全文层层推进,笔锋犀利,抨击十分有力。
此信开篇即称道郑子玄“质实有耻",而其所谓有耻者,则在于他“不肯讲学”,其言下之意大概说当今之讲学者都是“无耻”的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是他不曾亲见先秦颜(渊)、曾(参)、(子)思、孟(轲)诸贤,也不曾亲见宋代周(敦颐)、程(颢、颐)、张(载)、朱(熹)等理学宗师。仅从他所听到和看到的今之道学家的言行,便足以使他深感羞耻而绝不肯讲了。接着,作者以“不讲虽是过”这种退一步的笔法,将为何“学者耻而不讲”的缘故和罪过完全归结到“今之讲学者”的身上,并说他们“使学者耻而不讲”,断言其罪“可诛”,明确地表示自己对“今之讲学者”的憎恨态度。原来,今之讲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是一些虚伪的道学家;他们骗得高官巨富以后仍继续“讲道德,说仁义”,并说要以道德仁义“厉俗而风世”,其实始终都是虚伪的。郑子玄认为正是这些讲周、程、张、朱者才真正是最“败俗伤世者”,所以对他们“益不信,不信故不讲”。李贽最后归结道:“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从而又否定了前边所说的“不讲虽是过”之说。宋理学家大儒朱熹曾将人类历史划为“圣”、“凡”两境,三代(夏商周)以前属于“圣境”,“圣境”之人均无利欲、富贵的要求,是一个理想的境地。因此,朱熹十分推崇汉代经学大师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观点,即认为讲仁义道德的人是不言功利的。明代的道学家却口讲仁义道德而心系高官厚禄,在行为上违背了这个观点。因此,李贽不但明言此中人心口不一,而且将其一旦以不仁不义的手段获取高官巨富之后,却偏要假惺惺地大谈其仁义道德以掩盖其丑行的心态揭示于众。这里须指出的是,李贽此番批判绝无站在儒学立场上以维护其纯洁性之意,实乃借此攻击假道学之虚伪,不过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罢了。这里,作者不仅将假仁假义欺世盗名的道学家的本质彻底揭露出来,而且又点出了郑子玄不肯讲学的原因,从而泾渭分明地将学者分为“有耻”与“无耻”两类。以郑子玄与当今假道学家相比,后者之“无耻”便昭然若揭了。
然后,李贽极尽其讽刺之笔,以黄生为例,尖锐地揭露假道学家的骗术。他形象鲜明地将这个趋炎附势、厚颜无耻的家伙南来北往、“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死乞白赖地到处“抽丰”、索要财物的可贱可鄙形象活画出来。说到底,这位黄生不过是为了“好一口食难割舍”便两边讨好,两边炫耀,又两边行骗罢了。作者在这里借村言俚语写出那个黄生永无厌足的丑态是“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与上文“好一口食难割舍”遥相照应,极写其人灵魂的卑鄙污秽。而且在表现形式上也故意运用与道学家惯常使用的雅言相违的粗俗之语,以示自己纯属“异端”,与他们绝无共同之处。李贽用此句痛斥其丑行,极尽诅咒斥骂之能事,真是痛快淋漓,无以复加,足以使此辈掩面落荒而逃。此段黄生之例,虽似揭露黄生其人,而其目的则是借以批判“今之讲周、程、张、朱者”,故结语曰“今之道学,何以异此”,便把作者一腔忿懑之气完全倾泻在“今之道学”家身上了;并使这段与上段的若即若离而骤成有机整体,全在敷演与转接之功。接着,李贽又揭露并批判了道学家行骗的另一种方式——托名“圣人”或“山人”,改头换面地以欺世盗名,获取暴利。自古以来就有一些文人以“隐士”或“山人”自命,名为清高避俗,实则坐待入仕之良机;更有一些儒者自谓深得知善知恶的“良知”,大讲仁义道德而倍受统治者青睐。对这些人,李贽剖析了他们的居心和隐私,指斥他们“名山人而心商贾”之“可鄙”,乃至“掩抽丰而显嵩、少”的行为的“尤可鄙”。这是一层。再说那些以“圣人”自称的“今之讲道德性命者”,或“自称曰圣人”,或“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者,都不免“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都是黄生一类四处行骗的人物。这是又一层。经过这样深透的分析,可见郑子玄的不肯讲学,应为“质实有耻”而“可喜”了。既呼应了首段,又照应了二段,章法十分纯熟。这里,李贽非常独特地避用古典而自引比喻阐发事理,如以前文中交代清楚了的“掩抽丰而显嵩、少”比喻如黄生般行骗;以“游嵩、少者”喻“显者”;以“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喻一箭双雕的骗术等等,既避免了重蹈当时文人拟古、沿袭之复辙,又借代以亲见亲听之事,使文章更具有无可辩驳的说服力。
上段已说“名山人而心商贾,即已可鄙矣”,而在末段却开口便说“商贾亦何可鄙之有”。其实,前所言的“可鄙”,实指心口不一、名实不符的“山人”,非指商贾。李贽认为,“身履是事,口便说是事,作生意者但说作生意,力田作者但说力田作,凿凿有味,真有德之言。”(《答耿司寇》)全然没有什么可鄙。况且商贾“辛苦万状”,“受辱忍诟”,还要承担风险,既劳力又劳心,而所得却很微薄。“山人”则不同,他们“不持一文”本钱,“非公卿之门不履”,凭三寸不烂之舌而专事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事,他们早已“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童心说》),这些人才是最可鄙贱的。在此,作者的态度再明确不过了。最后,李贽以自己为例,明言若自己亦“存商贾之心”却披着仁义外衣而行欺世盗名之事,“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以示其与“失却真心”的假道学家斗争到底的决心。可见其襟怀之坦荡。此段紧承上段对郑子玄“不肯讲学”之赞许,进一步阐发了作者对假道学的厌恶。
这篇散文在分析问题、论证事理时所体现的复杂谨严、逻辑周密的思维特点是十分突出的。文章既具有丰富的形象性,又具有精湛的思辩性,表现出作者良好的文学素养和敏锐的逻辑思维能力。全文系书信体,语言朴素,笔到意随,而良友契厚,相知有素,倾怀畅谈,更无不尽之辞。李贽文章所具有的内容深厚和大胆的反潮流思想,在这篇文章里得到充分的体现,可视为其散文的典型之作。当然,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比这篇书信所能表达的要丰富得多,那就另当别论了。对于李贽的著作,封建统治者视为洪水猛兽,明清两代均曾多次禁毁过,这也可以证明他的进步思想是为封建统治者所深恶痛绝的。他的书却始终未能禁绝,而是一直流传至今,正说明人民对他的欣赏或赞同。恰如明末慈溪冯元仲所赞:“手辟洪蒙破混茫,浪翻古今是非场。通身是胆通身识,死后名多道益彰。”
参考资料:
1、黄岳洲,茅宗祥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名篇鉴赏辞典·明清文学卷.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6月:第102—105页
创作背景
李贽一生著作甚丰,其诗文集命名曰《焚书》。李贽《焚书》卷二有《又与焦弱侯》一信。此文应是万历己丑(1589年)下半年或稍后在麻城所作。根据是此信列在《复焦弱侯》之后,该信有“所望兄长尽心供职”之语,查焦竑万历己丑春中状元,授脩撰才在北京任职。此是郑子玄到麻城与李贽见面后李写给焦竑的信。参照《焚书》卷六《送郑子玄兼寄弱侯》五律所说“旅鬓迎霜日,诗囊带雨秋。蓟门虽落莫,应念有弱侯”,可旁证此信似写于深秋时节之后,当时焦竑正在北京。
参考资料:
1、陈泗东.幸园笔耕录.福建:鹭江出版社,2003年1月:第352页
又与焦弱侯
郑子玄者,丘长孺父子之文会友也。文虽不如其父子,而质实有耻,不肯讲学,亦可喜,故喜之。盖彼全不曾亲见颜、曾、思、孟,又不曾亲见周、程、张、朱,但见今之讲周、程、张、朱者,以为周、程、张、朱实实如是尔也,故耻而不肯讲。不讲虽是过,然使学者耻而不讲,以为周、程、张、朱卒如是而止,则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彼以为周、程、张、朱者皆口谈道德而心存高官,志在巨富;既已得高官巨富矣,仍讲道德,说仁义自若也;又从而哓哓然语人曰:“我欲厉俗而风世。”彼谓败俗伤世者,莫甚于讲周、程、张、朱者也,是以益不信。不信故不讲。然则不讲亦未为过矣。
黄生过此,闻其自京师往长芦抽丰,复跟长芦长官别赴新任。至九江,遇一显者,乃舍旧从新,随转而北,冲风冒寒,不顾年老生死。既到麻城,见我言曰:“我欲游嵩少,彼显者亦欲游嵩少,拉我同行,是以至此。然显者俟我于城中,势不能一宿。回日当复道此,道此则多聚三五日而别,兹卒卒诚难割舍云。”其言如此,其情何如?我揣其中实为林汝宁好一口食难割舍耳。然林汝宁向者三任,彼无一任不往,往必满载而归,兹尚未厌足,如饿狗思想隔日屎,乃敢欺我以为游嵩少。夫以游嵩少藏林汝宁之抽丰来嗛我;又恐林汝宁之疑其为再寻己也,复以舍不得李卓老,当再来访李卓老,以嗛林汝宁:名利两得,身行俱全。我与林汝宁几皆在其术中而不悟矣;可不谓巧乎!今之道学,何以异此!
由此观之,今之所谓圣人者,其与今之所谓山人者一也,特有幸不幸之异耳。幸而能诗,则自称曰山人;不幸而不能诗,则辞却山人而以圣人名。幸而能讲良知,则自称曰圣人;不幸而不能讲良知,则谢却圣人而以山人称。展转反复,以欺世获利。名为山人而心同商贾,口谈道德而志在穿窬。夫名山人而心商贾,既已可鄙矣,乃反掩抽丰而显嵩少,谓人可得而欺焉,尤可鄙也!今之讲道德性命者,皆游嵩少者也;今之患得患失,志于高官重禄,好田宅,美风水,以为子孙荫者,皆其托名于林汝宁,以为舍不得李卓老者也。然则郑子玄之不肯讲学,信乎其不足怪矣。
且商贾亦何可鄙之有?挟数万之赀,经风涛之险,受辱于关吏,忍诟于市易,辛勤万状,所挟者重,所得者末。然必交结于卿大夫之门,然后可以收其利而远其害,安能傲然而坐于公卿大夫之上哉!今山人者,名之为商贾,则其实不持一文;称之为山人,则非公卿之门不履,故可贱耳。虽然,我宁无有是乎?然安知我无商贾之行之心,而释迦其衣以欺世而盗名也耶?有则幸为我加诛,我不护痛也。虽然,若其患得而又患失,买田宅,求风水等事,决知免矣。
行路难三首
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
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闲来垂钓碧溪上,忽复乘舟梦日边。
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
羞逐长安社中儿,赤鸡白雉赌梨栗。(白雉 一作:白狗)
弹剑作歌奏苦声,曳裾王门不称情。
淮阴市井笑韩信,汉朝公卿忌贾生。
君不见昔时燕家重郭隗,拥篲折节无嫌猜。
剧辛乐毅感恩分,输肝剖胆效英才。
昭王白骨萦蔓草,谁人更扫黄金台?
行路难,归去来!
有耳莫洗颍川水,有口莫食首阳蕨。
含光混世贵无名,何用孤高比云月?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
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投湘水滨。
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
华亭鹤唳讵可闻?上蔡苍鹰何足道?
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
且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送杜十四之江南
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淼茫。(淼茫 同:渺)
日暮征帆何处泊,天涯一望断人肠。
菩萨蛮·花明月暗笼轻雾
花明月暗笼轻雾,今宵好向郎边去。刬袜步香阶,手提金缕鞋。画堂南畔见,一向偎人颤。奴为出来难,教君恣意怜。
谒金门·杨花落
杨花落,燕子横穿朱阁。苦恨春醪如水薄,闭愁无处着。
绿野带红山落角,桃杏参差残萼。历历危樯沙外泊,东风晚来恶。